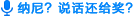1997年的6月30日,香港视为父兄的伦敦乘坐不列颠尼亚号离开了。他孤独地坐在礼堂的前排,等待着升旗仪式,这象征着主权的交接。他回到过广东的家乡,窥探过未来的人生,可是,窥探他人的人生和自己亲身经历,是不一样的。他看过那些法制不健全、民智未启蒙的惨痛,今天过后,即使躲回赛马场,“马照跑,舞照跳”竟被视为“恩典”,这一事实本身就让他心烦意乱。你们建国以后还曾经允许保留私营经济,然后公私合营取缔了他们。你们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,然后马上变成引蛇出洞。
我不相信未来会变好的。你们给我的信心不足以让我相信未来。
他知道大陆唯一一个有可能理解他的人在哪里,香港为坐标原点,目光指向东北,江苏的南边,浙江的北边。旧时华洋混居的乐园,80年代后老派复苏的东方魔都。你知道我的痛苦。你的过去很有可能是我的未来。
上海穿着以香港的眼光看稍显过时的西装,依然是日式风格的剪裁,日本人的西装最适合亚洲人的身材。是不是你从阁楼里翻出来的旧衣服呢?哈,你的鸭舌帽收了起来,圆礼帽也不让戴了,中山装,列宁装,据说你还穿过草灰色的军装。你有没有被人押着游街,有没有被人剃掉精心修剪的头发。为什么改开以后,门禁开放,你不愿意与我见面。骄傲的东方魔都,我怎会嫌弃你的颓败和没落。我同情你的遭遇。虽然你拒绝怜悯和同情。你是强者,依靠与他人战斗彰显自身。而所有人都知道,你被这个国家宠爱着,哪怕你再沮丧,它也不会放任对外的窗口维持难堪的样子。不出二十年,你会比我能想象的更加美好。只是你不愿意见我罢了。曾经,你在我面前是那样的不可逾越。可是,这世上并没有永恒之城,你没有维持当年在我面前的震撼,我也不会。我的友人,给我机会,让我和你一起见证未来吧。
突然,上海回过头来,迎上了香港的视线,他向香港招手,示意香港过来。紫荆花旗帜已经顺着歌声升上了顶点,香港无心去看。他不喜欢这个晚上。他走到上海跟前,试图自然的攀谈。可是,当他被吸引到上海身边后,上海退入人潮,消失不见。苏州、杭州、南京、扬州、温州,如同湿漉漉的黑色枝条,模糊的面孔。香港不明所以的被淹没。
他听到了熟悉的旋律,黎明破晓,朝阳初升,叮咚作响的河水声划破宁静,带来新生。舞台上出现了一群孩子们,童声合唱《东方之珠》。
“小河弯弯,向南流。流到香江,去看一看。”
“东方之珠,我的爱人,你的风采,是否浪漫依然?”
人潮推挤着,事先排练好的秩序。香港被簇拥着,沿着既定的轨迹,被推向了该去的位置。他走过一排排座椅,路过一排排的城市。眼神客气而礼貌的照顾摄像机,余光顺从心意扫视着现场,这个不是,那个也不是,普通的泯然众人,都不是他想见的那个人。
上海,你在哪里?
“月儿弯弯的海港,夜色深深灯火闪亮。”
“东方之珠,整夜未眠。”
“守着沧海,桑田变换的诺言。”
被改编过的歌曲。其实你们不知道吧,香港这座城市,是由不满自身命运的农民和渔民,还有在大陆混不下去的商人和文人建成的。“诺言”,这块土地被租约捆绑,而我作为人民意志的集合,出生于土地被租让以后,那个诺言没有我的参与,可我这个社会的命运竟然要由它左右。
突然,气流涌动,礼堂的大门被打开了。与舞台相对的方向,观众席的背后,响起了不一样的声音。少年即将变为青年男子的厚重嗓音:
“让海风吹拂了五千年,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。”
香港本能的转头望去,又客气而礼貌的换上惊讶和喜悦的表情。原来你们搞出这么多戏,是为了这个人。好吧。他心中泛起了对上海的失望。虽然上海也是这潮流之中无法反抗的一员。虽然上海刚才可能没有别的意图,只是让他到达指定地点方便节目的开始。
“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,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。”
深圳顺着长长的台阶,踩着拍子渐渐走近香港。这一段的歌词结束了。他停了下来。他来得晚,可是鲜花是不缺的。涂了大红脸蛋、戴着红领巾的童男童女从观众席中绕出,一个给他送上鲜花,一个向他敬礼。哦,可爱的□□主义的接班人。
下一段的歌词开始了:
“船儿弯弯入海港,回头望望,沧海茫茫。”
舞台两侧的侧门打开了,广东、福建等南方省份的城市鱼贯而出。
“东方之珠,拥抱着我。”
“让我温暖,你那苍凉的胸膛。”
深圳再次开始踩着节拍往下走,一步步踏踏实实的来到香港身边。由于炎热,他的额头上沁出细细的汗珠,可是依旧在卖力的唱着。离得近,香港听到了他的真实声音,没走调也没抢拍,高音部分居然还上去了。他练习过这首歌。你们都练习过。可是有必要吗?
香港恍然想起,哦,似乎真有必要,“团结”。大陆城市和香港合唱《东方之珠》,祈愿香港的未来,多么美妙的喜剧。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喜剧。
他主动接过深圳递给他的话筒,还有鲜花,顺着人群既定的轨道,走上舞台。
“让海风吹拂了五千年,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。”
“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,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。”
歌曲能够带给人力量,即使再不情愿,再觉得可笑,香港也承认,当大家簇拥着他合唱《东方之珠》时,他内心的力量被调动了。仿佛真的开始相信未来会变好。
人总要依靠一点信念活着。这空虚无聊的世间,幻想带给人力量。无论民族振兴还是国家富强,无论“崛起”还是“复兴”,有目标就有力量。
环境嘈杂,香港没有耳麦,依据深圳的口型判断唱到了哪里。香港眼瞳中倒映着年轻的深圳。深圳。你的眼神犹如出鞘的利剑,年少的君王。你的生活简单而直接,经济建设,崛起。你一无所有,任何积累都是成功,所以你顺风顺水。没有政治立场的拉扯拖累你,因为你没有选择。你没有文化根基,所以,你也不会由于多元文化的交融而迷茫,一切都是新的,你就像四处嗅闻的幼犬,发现新大陆的快乐。你是一张白纸,所以,你过得简单纯粹而快乐。
你多么单纯。你未曾遭受过我和上海曾经遭受的复杂选择。
1997年,深圳,这是你出生的第17年。
我知晓你的前世,你是深圳河畔的少女。你仰望我。因为贫穷和饥饿,你想要成为我。你跳进了深圳河,杀死了过去的自己。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好。你想要成为的不是香港,我住在“石屎森林”中的“鸽笼”里,睡在不能翻身的单人床上,青菜昂贵,浩南和山鸡在街头打架。你想要富足,想要吃饱饱。你想要手表和圆珠笔。你想听靡靡之音。你想成为的不是我,是未来的你。你的人民几次游过深圳河,冒着暴雨和洪水,还有被抓回去改造的风险。有的成功了,有的没有,失败的人死在了深圳河里。现在的罗湖桥口岸下方都是你的人民的尸体。奔向美好生活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失败的付出生命,成功的献出青春和血汗。他们到了香港以后只能做最低贱的工作,在工厂里工作16个小时。可是,宝安县一个农民每年20元收入,在工厂里一天就赚50块。
深圳,深圳,你懂得你出生前这块土地的苦难吗?你不懂得,深圳没有土生土长的深圳人,他们的祖辈还没有埋在深圳的墓园里,深圳是居住地而非家乡。真正的深圳人逃到了香港,剩下的饿死在了家里,没有逃到香港的死在了深圳河或者大鹏湾里。你的血脉汇入了广东人、湖南人,当然还有湖北人福建人和广西人。五湖四海的人。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你的博物馆是由全国捐赠的,香港也捐了几块骨头给你。你的历史被移到了东莞,东莞记得你的历史。
现在的“深圳人”记得的深圳的历史,是从离开故乡开始的,到达新土地。一开始他们仰望着二线关。二线关取消了,就开始仰望罗湖桥和福田,这是关口的名字。二线关里面是特区。特区后面是香港。
深圳,深圳,现在他们笑着问你能不能帮他们冲□币,因为马□腾的公司在你那里。其实应该问你会不会组装苹□手机,会不会把耳机线放进包装盒里。你的发家并不光彩。可是光彩不是你的追求,赚钱和吃饭才是。你承接了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,最脏最苦最累的活你愿意去干。我们当年也愿意。你就是过去的我们。
我不相信未来会变好的。你们给我的信心不足以让我相信未来。
他知道大陆唯一一个有可能理解他的人在哪里,香港为坐标原点,目光指向东北,江苏的南边,浙江的北边。旧时华洋混居的乐园,80年代后老派复苏的东方魔都。你知道我的痛苦。你的过去很有可能是我的未来。
上海穿着以香港的眼光看稍显过时的西装,依然是日式风格的剪裁,日本人的西装最适合亚洲人的身材。是不是你从阁楼里翻出来的旧衣服呢?哈,你的鸭舌帽收了起来,圆礼帽也不让戴了,中山装,列宁装,据说你还穿过草灰色的军装。你有没有被人押着游街,有没有被人剃掉精心修剪的头发。为什么改开以后,门禁开放,你不愿意与我见面。骄傲的东方魔都,我怎会嫌弃你的颓败和没落。我同情你的遭遇。虽然你拒绝怜悯和同情。你是强者,依靠与他人战斗彰显自身。而所有人都知道,你被这个国家宠爱着,哪怕你再沮丧,它也不会放任对外的窗口维持难堪的样子。不出二十年,你会比我能想象的更加美好。只是你不愿意见我罢了。曾经,你在我面前是那样的不可逾越。可是,这世上并没有永恒之城,你没有维持当年在我面前的震撼,我也不会。我的友人,给我机会,让我和你一起见证未来吧。
突然,上海回过头来,迎上了香港的视线,他向香港招手,示意香港过来。紫荆花旗帜已经顺着歌声升上了顶点,香港无心去看。他不喜欢这个晚上。他走到上海跟前,试图自然的攀谈。可是,当他被吸引到上海身边后,上海退入人潮,消失不见。苏州、杭州、南京、扬州、温州,如同湿漉漉的黑色枝条,模糊的面孔。香港不明所以的被淹没。
他听到了熟悉的旋律,黎明破晓,朝阳初升,叮咚作响的河水声划破宁静,带来新生。舞台上出现了一群孩子们,童声合唱《东方之珠》。
“小河弯弯,向南流。流到香江,去看一看。”
“东方之珠,我的爱人,你的风采,是否浪漫依然?”
人潮推挤着,事先排练好的秩序。香港被簇拥着,沿着既定的轨迹,被推向了该去的位置。他走过一排排座椅,路过一排排的城市。眼神客气而礼貌的照顾摄像机,余光顺从心意扫视着现场,这个不是,那个也不是,普通的泯然众人,都不是他想见的那个人。
上海,你在哪里?
“月儿弯弯的海港,夜色深深灯火闪亮。”
“东方之珠,整夜未眠。”
“守着沧海,桑田变换的诺言。”
被改编过的歌曲。其实你们不知道吧,香港这座城市,是由不满自身命运的农民和渔民,还有在大陆混不下去的商人和文人建成的。“诺言”,这块土地被租约捆绑,而我作为人民意志的集合,出生于土地被租让以后,那个诺言没有我的参与,可我这个社会的命运竟然要由它左右。
突然,气流涌动,礼堂的大门被打开了。与舞台相对的方向,观众席的背后,响起了不一样的声音。少年即将变为青年男子的厚重嗓音:
“让海风吹拂了五千年,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。”
香港本能的转头望去,又客气而礼貌的换上惊讶和喜悦的表情。原来你们搞出这么多戏,是为了这个人。好吧。他心中泛起了对上海的失望。虽然上海也是这潮流之中无法反抗的一员。虽然上海刚才可能没有别的意图,只是让他到达指定地点方便节目的开始。
“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,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。”
深圳顺着长长的台阶,踩着拍子渐渐走近香港。这一段的歌词结束了。他停了下来。他来得晚,可是鲜花是不缺的。涂了大红脸蛋、戴着红领巾的童男童女从观众席中绕出,一个给他送上鲜花,一个向他敬礼。哦,可爱的□□主义的接班人。
下一段的歌词开始了:
“船儿弯弯入海港,回头望望,沧海茫茫。”
舞台两侧的侧门打开了,广东、福建等南方省份的城市鱼贯而出。
“东方之珠,拥抱着我。”
“让我温暖,你那苍凉的胸膛。”
深圳再次开始踩着节拍往下走,一步步踏踏实实的来到香港身边。由于炎热,他的额头上沁出细细的汗珠,可是依旧在卖力的唱着。离得近,香港听到了他的真实声音,没走调也没抢拍,高音部分居然还上去了。他练习过这首歌。你们都练习过。可是有必要吗?
香港恍然想起,哦,似乎真有必要,“团结”。大陆城市和香港合唱《东方之珠》,祈愿香港的未来,多么美妙的喜剧。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喜剧。
他主动接过深圳递给他的话筒,还有鲜花,顺着人群既定的轨道,走上舞台。
“让海风吹拂了五千年,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。”
“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,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。”
歌曲能够带给人力量,即使再不情愿,再觉得可笑,香港也承认,当大家簇拥着他合唱《东方之珠》时,他内心的力量被调动了。仿佛真的开始相信未来会变好。
人总要依靠一点信念活着。这空虚无聊的世间,幻想带给人力量。无论民族振兴还是国家富强,无论“崛起”还是“复兴”,有目标就有力量。
环境嘈杂,香港没有耳麦,依据深圳的口型判断唱到了哪里。香港眼瞳中倒映着年轻的深圳。深圳。你的眼神犹如出鞘的利剑,年少的君王。你的生活简单而直接,经济建设,崛起。你一无所有,任何积累都是成功,所以你顺风顺水。没有政治立场的拉扯拖累你,因为你没有选择。你没有文化根基,所以,你也不会由于多元文化的交融而迷茫,一切都是新的,你就像四处嗅闻的幼犬,发现新大陆的快乐。你是一张白纸,所以,你过得简单纯粹而快乐。
你多么单纯。你未曾遭受过我和上海曾经遭受的复杂选择。
1997年,深圳,这是你出生的第17年。
我知晓你的前世,你是深圳河畔的少女。你仰望我。因为贫穷和饥饿,你想要成为我。你跳进了深圳河,杀死了过去的自己。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好。你想要成为的不是香港,我住在“石屎森林”中的“鸽笼”里,睡在不能翻身的单人床上,青菜昂贵,浩南和山鸡在街头打架。你想要富足,想要吃饱饱。你想要手表和圆珠笔。你想听靡靡之音。你想成为的不是我,是未来的你。你的人民几次游过深圳河,冒着暴雨和洪水,还有被抓回去改造的风险。有的成功了,有的没有,失败的人死在了深圳河里。现在的罗湖桥口岸下方都是你的人民的尸体。奔向美好生活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失败的付出生命,成功的献出青春和血汗。他们到了香港以后只能做最低贱的工作,在工厂里工作16个小时。可是,宝安县一个农民每年20元收入,在工厂里一天就赚50块。
深圳,深圳,你懂得你出生前这块土地的苦难吗?你不懂得,深圳没有土生土长的深圳人,他们的祖辈还没有埋在深圳的墓园里,深圳是居住地而非家乡。真正的深圳人逃到了香港,剩下的饿死在了家里,没有逃到香港的死在了深圳河或者大鹏湾里。你的血脉汇入了广东人、湖南人,当然还有湖北人福建人和广西人。五湖四海的人。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你的博物馆是由全国捐赠的,香港也捐了几块骨头给你。你的历史被移到了东莞,东莞记得你的历史。
现在的“深圳人”记得的深圳的历史,是从离开故乡开始的,到达新土地。一开始他们仰望着二线关。二线关取消了,就开始仰望罗湖桥和福田,这是关口的名字。二线关里面是特区。特区后面是香港。
深圳,深圳,现在他们笑着问你能不能帮他们冲□币,因为马□腾的公司在你那里。其实应该问你会不会组装苹□手机,会不会把耳机线放进包装盒里。你的发家并不光彩。可是光彩不是你的追求,赚钱和吃饭才是。你承接了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,最脏最苦最累的活你愿意去干。我们当年也愿意。你就是过去的我们。